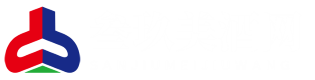冬日是不是读诗的季节?我常在冬夜里想到翻诗,读诗让我想到许多事。不是人人耽酒的,白居易爱的是一个“晚来天欲雪”的黄昏,去邀一位故人来赴“红泥小火炉”的约会的情趣。那位叫刘十九的朋友或赴约,或不赴约,我们只读到千年前那一点点的闲情雅兴,那夜的酒早已挥发,不朽的是那一片情怀。
而元曲中的刘致也用“瘿瓢,带槽”去舀酒的句子来刻画村酒的原始粗犷:一只疙疙瘩瘩的葫芦瓢,狠狠地伸入酒缸,连糟带酒,胡乱地舀起来就喝,自有一番金杯玉盏之外的豪情。
关汉卿的句子尤其迷人:旧酒投,新醅泼,老瓦盆边笑呵呵,共山僧野叟闲吟和,他出一对鸡,我出一个鹅,闲快活。
那样的饮酒情趣又岂在饮?
中国诗人好像都是如此。他们爱花,但爱的是花所能完成的隐逸、高洁或烂漫的意象;他们爱月,但爱的是故乡的或故人的联想;他们爱玉,但永远不愿以克拉计算它的价值,因为它是用来象征“君子之德”的(由于它的致密、坚实、润泽);他们爱马,爱的是那种振鬣长鸣,万谷回应的雄风。
记得陶渊明吗?他幽默地给自己做了一张无弦琴,并且题诗曰:“但识琴中趣,何劳弦上声。”他爱琴,爱的竟是众弦寂然之后的“琴趣”。
生命,何尝不是一样呢?所有人都恋栈生命,但我们真正深爱的,是生命中的什么呢?
如果生命是一瓮酒,我们爱的不是那百分之几的酒精成分,而是那若隐若现的芬芳。
如果生命是琴,让我们忘记这长达一百六十厘米或一百八十厘米的梧桐木,我们爱的是音符和节拍之上的音乐——文章来源华夏酒报也许别人听不到,但我们知道,它在那里。在一个小小的划拨的动作里,可以触动多少音乐啊!
如果我们爱生命,也必有什么是在这血、肉、脂肪、皮肤、毛发之外的美好。我这样说,你能同意吗?我不是说酒不够美,我是说美酒之外必然还有什么饮趣。
有人说:“看得见的是暂时的,看不见的是永久的。”我们喜欢自己这健康的、有弹力的身体,但我们更爱的是这身体之外的一种更动人的什么……
我因而相信心灵,相信灵魂。
你能同意吗?如果我们相信饮趣比酒更重要,我们就有理由相信,必有什么是比这七尺之躯更昂然、更敏锐、更美好的。
转载此文章请注明文章来源《华夏酒报》。
要了解更全面酒业新闻,请订阅《华夏酒报》,邮发代号23-189 全国邮局(所)均可订阅。